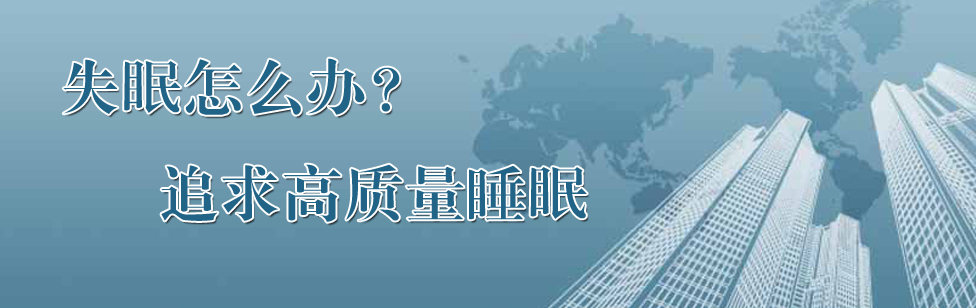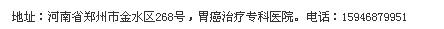“我想要拍扫大街的人,而不是扫大街这件事。”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在年的秋天,我认识了一个电影迷朋友,他不停地向我推荐一部名叫《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的电影,大肆渲染这部电影有多吊。而从小就喜欢内裤外穿的超人的我对蝙蝠侠并不是很感冒,加上也找不到资源,就一直没去看这部电影。当他告诉我这部电影的导演的名字的时候,我只觉得拗口得很,花了很久才能正确说出他的名字——克里斯托弗·诺兰。过了一段时间,和那个朋友失去了联系,想起他来时,就想起了诺兰,于是下载了他的一部电影来看,那部电影叫《记忆碎片》。看完后我整个人惊呆了,电影怎么还可以这样拍?接着陆续把他之前的电影全找出来看完了,他之后的电影一部也没有错过。诺兰的新电影《信条》上映已经上映了几天,我在上映第二天就去看了,看完后心情很平淡,平淡到虽然没看明白,但竟然没有想要去弄懂电影到底在讲什么的冲动,这是我在看诺兰以往电影没有过的体验。可能诺兰在看过成片后,自己都好像没咋搞明白,所以他在台词里,委婉地告诉了观众如何正确地观看这部电影。从初露锋芒的《追随》开始,诺兰就奠定了自己独特的电影美学——迷宫式叙事,即用非线性结构去讲述一个线性故事。这种非线性结构的运用,还有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昆汀·塔伦蒂诺和盖·里奇,而库布里克在他的《杀手》结尾,也早已经尝试着就同一事件,展现不同人的视角,很难说这哥仨没受到库布里克的影响。杀手(年)而诺兰的迷宫式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故事中的人物置于迷宫之中,人物在迷宫中不停地寻找出路,以至于越来越迷失自己,成为了一个无路可走的迷途者。纵观诺兰以往的电影,主角的身份设定往往有极强的的双重性,《追随》中无所事事的小说作者藉由观察别人尾随他人,最终发现自己才是被尾随的那个;《记忆碎片》中的保险推销员追杀死妻子的凶手,到头来却意识到妻子的死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失眠症》中的警察为了将犯人定罪,自己却犯下了罪行;《致命魔术》中的两个魔术师,既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又是彼此憎恶的对手;《蝙蝠侠前传》中的蝙蝠侠一方面是处于聚光灯下的上流富豪,一方面又是只能隐迹于黑暗中的正义英雄:《盗梦空间》中的造梦师被梦反噬,以至于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星际穿越》中的宇航员为了给全人类找到合适的家,舍弃了和女儿的家。刨除诺兰电影中各种宏观的概念,每个角色身份的设定,都是基于微观个人的情感体验基点,其具有的对立与统一性,最大限度地建立起了戏剧冲突性,但从没有丧失掉真实性。诺兰电影的魅力在于,他用这些概念规划好迷宫图纸,让人物自己拿着图纸去构建迷宫并且陷入迷宫之中,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会跟随着人物一起去经历走进迷宫的过程。诺兰近几年越来越向真实性靠拢,尤其是上一部《敦刻尔克》,更是选择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在《敦刻尔克》中,诺兰用自己善用的结构,通过士兵,民用救援船,飞行员三条线来讲述这一历史事件,电影抛弃了一些过于花哨的技巧,通过平稳的叙事瞄准了在那场战争中的平凡的人物的处境。可能是《敦刻尔克》反响一般,到了《信条》,诺兰重新又回到之前的风格,整部电影分钟看下来,虽然不会很累,但是觉得很无趣,最大的感受就是像看了一部《》。男主角,虽然设定是CIA,但是随着故事的进行,我不禁怀疑,CIA的门槛这么低吗,只要敢嗑药,就有资格拯救世界。你不是要去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大长腿的命比世界毁灭还重要啊。好,《信条》就说到这,再说说那位朋友推荐的《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作为一个毫无顾忌的纯粹的恶出现,来挑战着蝙蝠侠的善的底线,亲手建造了一个关于善与恶的迷宫,把蝙蝠侠囚禁在其中,让其在里面对自己所坚持的善产生怀疑。蝙蝠侠毕竟也只是个叫布鲁斯·韦恩的人类,人类的情感都是复杂的,他只能在这种困境中选择一条路走下去。这部电影的意义不是在界定善与恶,而是用一种思辨的方式来讨论善与恶,就像电影结尾,一直坚信正义的检察官开始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当诺兰的电影中没有了人物,只剩下概念的时候,就成了观众看完电影后造梗的源泉,这样的电影离真正的爆米花电影就也不远了。不过,还是期待诺兰的下一部电影,以及李安的下一部电影。白色条纹的黑斑马今晚泡面加不加卤蛋,就看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