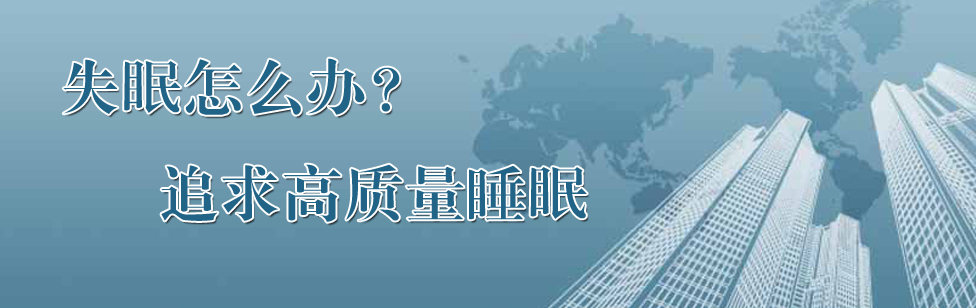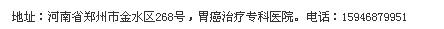看实验电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
昨天下午在栗宪庭电影基金连看了四部“反电影”,我并不知道这个“反电影”是什么意思!
是反技术、反故事、反常规,还是反艺术、反类型呢?
大概是我的屁股生了根,和我同去的三位看了不到二十分就离场了,中间回来两次,还是睡着了,只好拿着背包真的走了。
我也睡着了,但时间不长,原因是我根本不困,怎么会睡着呢?
我大约是全场看的最认真的一个,看了有四个半小时。
这是个全民拍电影的时代,一部手机一台家用dv,所有能拍视频的机型都可拍“电影”
可此电影非彼电影,电影是什么?
我们最熟悉的安德烈巴赞,以他为代表的电影影像本体论,高举“真实”大旗,推崇现实主义;他激烈的指责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理论,他认为蒙太奇控制下的电影太过于主观,令观众失去了判断,蒙太奇是文学化的语言,是最反电影的方式。在这里巴赞所说的“反电影”,是反对剔除忽视电影的纪录和再现特性。
巴赞认为电影应该给予观众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也就是真实客观的再现一个事件的方方面面,让观众自我判断自我解读,每一个不同的观众获得的不同感官体验和认识意义才是最有意义的,才是电影的本质。他明确的反对创作者利用电影的方式过分表达私欲表达自我情绪。所以他又创立了长镜头理论,用以反对蒙太奇至上论,强调现实的多义性。
再说爱森斯坦,他本身就是一位想法惊奇的电影导演,他在实践中提出蒙太奇理论,又不断的自我否定,最后他还是认为电影就是以镜头为单位的,一个镜头连接另一个镜头产生的寓意观感应该是镜头之积而不是简单的相加求和。他兴奋于可以利用蒙太奇带领观众体验电影的奇妙,观众可以不用思考轻松的跟随,或者边思考边追随,最后创作者与观众站在一起,看同一个战舰波将金号。然而观众和爱森斯坦想法无所谓统一,如此一来也许可以启发观众得到又一种神秘体验,只有观众自己知道。
在电影发明之初,电影是什么也在不断互怼不断理性与感性认识当中前进着,就巴赞和爱森斯坦,一个像老学究一个似艺术家,一个理性过头一个感性过头,谁都不服。但没有关系,电影就是电影,不是电影就不是电影。
电影不断的技术升级,不断的被各方创造者和理论家,不断的重塑真身。例如巴拉兹着迷特写,克拉考尔的电影化观点“物资现实的复原”。
说到物资现实的复原,电影《长江图》导演杨超在某讲座上数次提及“物资现实的复原”,找到一个“电影化”的故事,用一种“电影化”的结构拍一部“电影化”的电影。长江图上映之时,我正在片场劳碌,无缘大荧幕观影,之后下载的电影画质太差看不下去,至今无缘看得电影《长江图》;就克拉考尔这一电影观点,杨超导演找到的“电影化”叙事,可能就是时空错位,另俩个主人公,在穿行长江途中,不断相遇不断摸出花火不断发生故事。这样的结构魔幻现实成了电影化的手段和有趣之处吧?
忽然想起杨超导演在“物资现实的复原”中提到表演,说起一个观点或叫心得,他说(大意)汤唯在电影《色戒》中的自我牺牲在于性爱的部分,汤唯在镜头下复原了现实中做爱的经验和感官享受,使得她的表演令人信服,使得《色戒》中最最重要的这场床戏有了深层次的含义和作用。
那么电影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技术不断发展,3d4k帧,还有vr等等技术的出现,电影也在不断的在不同文化中“被发明”着。可以武断来说的是,无论那种形式无论那种观点下,拍一部好电影,能让人看下去的电影,至关重要。
如果只是自我实验品,还是成熟一些再拿出来为好!
下面是我看这四部所谓“反电影”的记录:
不要侮辱莫札特和山海經啦
拆篋、對話、記憶、無聊的鏡頭
對一個空間做長時間專注的觀察,
基耶羅夫斯基,哭得時候會關上一個門。
年輕的女生幼稚的喜歡,本質上紀錄片是電影?
周圍的觀察和很遠的紀錄
聯繫密切的事件
紀錄片一部分的紀錄
記實?恰恰是虛構的?
西遊記?
古典音樂與此空間貼切?
膚淺的東西要用噪音來烘托嗎?
音樂還是電影?
不覺得電影很重要!噪音?
內容強於音樂?
这四部名曰《八卦》、《建筑考》、《折线》、《来客ab》的所谓电影,还停留在“创想”的阶段,随意、为反而叛逆、当代行为艺术的延伸、试听造作的实验,和三位导演不修边幅的发型着装相得益彰。
切勿用艺术家三个字亵渎艺术,切勿用导演两个字抹黑电影。
写到这里,我发现他们所说的“反电影”,是反商业反文艺反实验片的视频影像。
毕竟,电影还是需要让人看下去的,无休止的强奸耳膜,无所谓的画面定格、无逻辑的自我催眠,这是电影嘛?
大概只对失眠症患者有帮助吧!
(本文观点,仅为参考)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