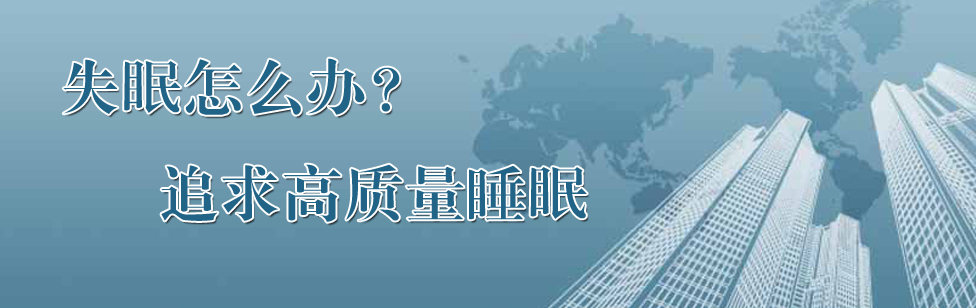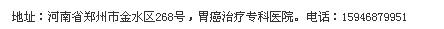点击↑蓝字即可订阅
源
四味毒叔文
四味毒叔
时间:年8月22日
地点:万达影院CBD店
主题:《敦刻尔克》导演见面会
嘉宾:主持人周黎明、《敦刻尔克》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中国导演黄建新
——电影《敦刻尔克》中外导演见面会
周黎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参加今天下午的中外导演交流会,我是主持人周黎明。
我们大家都知道电影是一个造梦的机器,特别擅长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的梦幻、梦想给展现出来。但是电影它同时也是非常擅长重现历史,再现曾经的光荣和梦想,一些真实的痛苦和不堪。
我们先请出我们中方的导演,著名导演、著名监制黄建新先生。
周黎明:黄导,您执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是监制,这三部影片我们都知道是宏大的叙事,历史题材。您在处理这样的题材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怎么样平衡重现历史跟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
黄建新:每次准备的时候就发现怎么从电影叙事的角度记录历史事件,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好在这三个题材都是以“建”字开始,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这个就给艺术想象留出了一个补充的空间,另外因为历史上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角度。
周黎明:您怎么评价《敦刻尔克》?
黄建新:诺兰导演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个月初的时候在香港就先到电影院去看了。
这是一部独特的电影,因为诺兰导演的电影永远有独特在其中,这里的独特是一小时、一天、一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设计。虽然是一个写实的背景,但是他依然保留了他极强的个人风格,非常稳健的叙事和艺术的张力,包括听觉系统的设立,都会慢慢的到最后震撼你,非常非常喜欢。
周黎明:刚才朋友们都看了这个影片,我们借这个机会,把诺兰导演呈现给我们的故事跟画面很简短的回顾一下,请看大银幕。
(短片)
这是专门给中国影迷剪辑的短片,下面有请《敦刻尔克》的导演,请大家跟我一起欢迎克里斯托弗·诺兰。
周黎明: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您似乎对空间时空这个概念非常的感兴趣,是您相信相对论吗,还是说您有自己的关于时间的理论?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是相信相对论的,但是对我来讲电影叙述故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所有的电影都希望让观众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能思考和感受一下时间的概念。
周黎明:黄导在您看过的诺兰先生的电影当中,您觉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艺术风格把它们串联在一起的?
黄建新:从他最早的《记忆碎片》,到后来看他的几乎所有的电影我都意识到你刚才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诺兰导演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和联系。
比如说《敦刻尔克》他的一小时、一天、一周,他这三个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的使用,然后就打乱了白天和晚上顺序,保持了观众对剧中事情和人物的心理上的准确的理解,那个维度上的最准确的点。
因为《敦刻尔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跟诺兰导演之前的故事不一样,在一个历史真实的发生的故事里本来时间线是一个A到B的时间点,诺兰导演为什么还是把它分成三个东西交叉起来来做。
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个故事是我从小就知道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故事是英国人都很熟知的,大家也讲敦刻尔克精神。所以这个电影它可以向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国际观众讲述这个故事,我非常荣幸能够向这么多的观众展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大家在英国众所周知的故事,但是我对于如何体验这个故事的视角是我个人的视角。
我希望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故事,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让观众有非常悬疑、非常紧张的感觉,而不是想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或者是政治课。我是希望观众能够与电影当中在沙滩上的角色、在飞机上、船上的角色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希望观众能够去想象一下如果他在当时的历史时刻是怎样的。
周黎明:您并没有讲太多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背景,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我并不是很了解英国的历史,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障碍吗?实际上反倒没有问题,不仅仅没有问题,反倒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并不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样的。
但是您刚才也说在英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的事件,当您在写剧本的时候,您在脑子当中有没有想象过不同的观众对影片的感受?
克里斯托弗·诺兰:因为有一些人是知道这个历史事件的结局的,也有很多像中国人一样,是不知道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你是如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人知道结局是怎样,有些人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能够创造出一种感觉,让观众观看时有一种现实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正在发生。
那些知道历史事件结局的人依然在看的时候有一种悬疑的紧张的感觉,对英国人来讲他们看的时候也会担心,到底这些人结局如何?就像看《泰坦尼克号》一样,你知道这个船会沉下去,但是你还是想看。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让观众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只要能创造出这个感觉就能让观众有一种悬疑的感觉,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你们不知道这个历史反倒更好,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感知这个历史的事件,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荣幸。
黄建新:按一般来讲写一个战争一定要写双方惨烈的对立面,和军队的出现,诺兰导演采取了一个特别极端的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军,在这样的风格设计里跟我们以往理解的战争电影是不同的,在这个电影里他是有意为之,还是他想创造另外一个他想触摸的更深的东西?
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个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做的决定,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想着不想展现敌人的近距离的面孔,我希望通过迫击炮、战机还有轰炸机等等的方式来展现,我希望人们有一种自己就在沙滩上的感觉。
我不希望把《敦刻尔克》拍成另外一部战争片,这是一个关于撤离的故事,所以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关于逃离的悬疑惊悚电影,而不是战争片。所以我不显示敌军的面孔,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像自己是沙滩上的士兵一样感觉到威胁,我觉得看不到敌人的面孔反倒更害怕,我希望让观众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你可能只是在很远的地方能够瞥见一些敌人。
周黎明:在您做研究的时候肯定看到过很多真人的故事,而且他们的故事要转变为电影的语言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你会决定创造一些虚拟的虚构的人物,而不是用真人真事呢?这些人物的形象是很多真人事迹组成的吗,还是有原形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采用虚构人物的决定是基于我的研究,我看到很多一手的资料,作为编剧我非常了解要讲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故事的话是需要深刻的人物的塑造的。
所以我读过这些人物事迹之后,我觉得直接把他们的故事搬上银幕的话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觉得反而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更容易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才决定创造一些虚构的人物。
既然有一些是虚构的人物那就所有的人物必须是虚构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有真人原形的,很多历史学家还有专家他们可以在电影当中找到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
我不想让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在一起互动,所以这样就让我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去写剧本,去引导观众让他体验敦刻尔克撤退的事件,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共鸣。
黄建新:我偶然翻到一个资料说,这个电影其实是诺兰最初当导演的时候就想拍的,放了非常长的时间,很多年以后他才开始拍这个电影,原因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之前也说过这个故事是我从小就听过的,您说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大概22年前的时候,艾玛·托马斯和我就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到达了敦刻尔克,也是行驶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当中人们同样的路线。
当时我们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旅程是非常危险的,水流很急,而且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跨越英吉利海峡,因为当时的自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如果说在战争的时候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话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的,所以我非常地敬佩这些士兵,在当时我就决定要拍这样一个电影。
但是后来我看到了很多的一手资料,以及真人叙述的书,我们开始讨论怎么把它变成电影。因为对英国人来说大家觉得这个显然是非常容易就能拍成电影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拍的时候你需要填补一种空白,你需要讲的故事此时还没有被讲出来,所以我就想用什么方式呈现它最好呢,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长的。
拍这么大规模的一部影片,这是一个宏大的故事,涉及到几十万人,有几百艘船,几百部战斗机。所以作为导演来说,你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能够把这样宏大的故事呈现出来。
十年前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自信,现在我有了,对英国的观众来说,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个电影只能拍一次的话,就一定要拍好。
周黎明:在电影当中您呈现了很多的细节,但是又避免了很多的人情世故的一些东西,这是英国的特色吗?
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的,对于在英国的电影当中,不大愿意呈现这些多愁善感的故事。我用的一些技巧是美国好莱坞的方式,原因就是故事本身是充满了情绪的,是一个非常情绪饱满的故事。
所以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你需要一种简单的、一种冷静的客观的视角去处理它,反映这个历史的事实,让这个历史的事实承载这个情绪。
我觉得人们或者是观众来说他们的同情心应该是通过他们看这些人物角色的命运来感受的,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给大家呈现一种真实感,这样如果大家能够相信这个故事,到看完电影之后最后不会太伤感,而是一种情绪上的满足。
黄建新:深深感受到诺兰导演说的这些设计和传达,比方说我记住了很多镜头,我记住了将军在栈桥上回头看去,几百艘小船在救英军之后的那一瞬间。我记住了火车上那两个士兵不敢看外头,低着头,窗外敲窗户,再敲,抬起头来一个老人手里拿着啤酒,笑着欢迎他们归来,那个时候我也流泪了,我感受到了在战争环境所有人性的最宝贵的东西。
因为要传达这样一种最真实的感觉,在拍摄上诺兰导演特别反对直接用很多的CG,导演是怎么展现这些动人心弦的镜头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的感受就是在拍历史事件的时候,摄影语言以及你所采用的镜头,这种基调必须是真实的,让你感受到你就在那里,你可以闻得到、听得到、看得到周围的事情。
所以这种特效的处理或者是动画等等是一种非常人工的东西,有一些故事是高于现实的,所以必须采用特效呈现。但是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我觉得需要一种非常朴实的方式,一种可以触摸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们用真正的故事、真正的船只,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只在某些场合用视效,比如说飞机那里拍摄的镜头合在一起,用了一些特效,主要是2D的技术,而不是用的数字的特效。
我想不起来用了多少视觉上的特效,其实不管怎么做都不能影响到整个影片真实的基调,我们的视觉特效师他在旁边一直观看摄像机里的镜头,希望能够通过摄像机捕捉到这些真实的画面。
周黎明:在《建军大业》和《敦刻尔克》里,你们都用了很多的年轻的面孔,以前都没有表演经验的年轻演员,你们是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还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
克里斯托弗·诺兰:对我来说,我是不想犯好莱坞大片的错误,就是找一个40岁的演员演一个很年轻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在战争当中的冲突非常真实的,有很多十八九岁的小孩上战场去打仗,所以需要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新鲜的面孔来呈现这些角色。
比如说汤米的扮演者菲恩·怀特·海德,据我希望在大家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演员,马上从人性的角度上感受到他想生存下去,并不见得他作为一个英雄,仅仅是想活下来而已,我想让观众和他一起体验这个历程。
黄建新:这个想法跟《建军大业》用年轻演员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是我的一些小朋友们说你要跟诺兰导演见面,能不能帮我们问一问他为什么那么迷恋胶片?
克里斯托弗·诺兰:如果你在拍电影的时候要呈现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经过风格化的感受,对我来说用电影的胶片是呈现这种效果是最佳的选择,它的颜色、清晰度等等是非常真实的。
对我来说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品质,它能够呈现出来我所看到的世界,所以它给我们的感受应该是正确的一种技术应用在这部电影里。
周黎明:另外你也说观众最好到影院里看这部电影,最好是在IMAX的影院看,我完全理解对于看《敦刻尔克》这样的电影应该在大屏幕上看,但是对于像《记忆碎片》等等,可不可以在家里看DVD呢?
因为有很多的细节的在电影里看的话只看一遍是看不懂的,可能需要多看几遍?所以你对一些家庭影院或者是网上直播的服务也可以欣赏你的影片有何看法?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觉得我可能是第一代的导演,自己从小在家里拿个摄像机就在家里,80年代的就开始拍片了。我从小看的这些电影,看了很多片的电影都是用胶片拍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影院里体验拍摄的电影。
当然如果说你希望再看一遍的话,我欢迎你在电影院里再看一遍,或者是在家里电视再看一遍或者是出了DVD再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在影院里才能看到这种深度。
因为我从小成长起来的时候,即便是一些你不喜欢的电影,有的时候你也看了三四遍,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飞机上、酒店里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所以我希望拍摄的电影能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感觉。
黄建新:作为电影导演都是这么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电影作品都能在电影院里看,但是诺兰导演的电影还有一个特点,很多人说看的时候有点看不懂,需要看一遍倒回去再看一遍,所以看的时候不是一个时间线看完了,是中间倒好几遍,对这样的一种阅读的方式导演怎么想?
克里斯托弗·诺兰:根据我对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在人的注意力,在一个周围昏暗的影院里或者说在家里你可以控制你看片的速度是不矛盾的。如果你原来在电视里看录像片,中间中断了,你要去打电话,回来就看不到大概有四五分钟就看不到了。
所以很长时间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样子的,比如奥逊·威尔斯之前拍的这些影片,他是非常复杂的叙事结构,当时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要在银幕上去看的,如果来影院看的话就会关掉手机,关掉手机就会非常北京中科医院爆光北京中科医院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