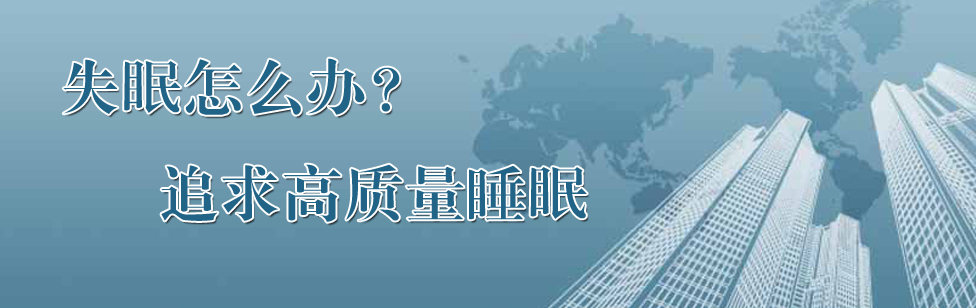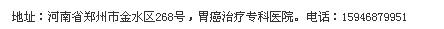黄河文学原创频道
作者简介
李鹏,山西垣曲人,现供职于县政府机关,工作之余喜欢读书、思考,写作。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叫母亲。无论这个人如何,你都是无权也无法选择的。母亲是女儿,是妻子,是祖母,是曾祖母。母亲失眠至今已44年了。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若不是怕给你们脸上抹黑,真想喝点药早点死去。我曾有过几次失眠,很难受。妻和妹妹也曾失眠过,也说很难受。可母亲这么些年天天面对漫漫长夜,我知道她真的是太难受了。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三大主要领导人先后去逝,唐山大地震、吉林陨石雨,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恐慌。那年,我家也发生了三件不幸的事:一是爷爷被房檐上突然掉下的豆腐架子,砸伤鼻梁血流不止;二是父亲上山伐木头,把脚砍伤血凝泥鞋;三是只有六岁的二弟马红彪得病夭折。红彪的突然离去,对母亲的打击很大。那年腊月二十三,家里为迎新年进行大扫除,母亲让红彪去河里刷一个沾满灰尘的竹篦。农家孩子懂事早,弟弟很快就按母亲的吩咐,把篦子刷得干干净净,拿回来后,还高高兴兴地晾到了我家院里的窗台上。忙忙碌碌的一家人,期盼着能过个好年。可没想到,弟弟晚上竟然开始发高烧,一直喊着爸爸妈妈要水喝。山里孩子感冒是常事,劳累一天的父母喂弟弟喝完水后也没太当回事,第二天父母一如既往地家里家外忙活着,弟弟在床上躺着。直到邻居大妈前来摸了摸孩子的头才发现情况不对,说孩子烧得这么厉害,你们怎么不叫医生?!这下父母才慌了,急忙把正在别人家看病的村医叫了过来。当时山村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村里只有一个民间医生,既给人看病也给兽看病,百姓得病基本靠扛和民间偏方,扛不住才叫医生,实在是要命的大病,才急忙绑个担架抬上医院送,往往是人到半路就不行了。医生来了后,摸了摸孩子的头,看了看舌苔,说是重感冒,要退烧,但药盒里又没有药,父母只有走遍全村才借来几支退烧针,注射后烧退了点,但很快又反弹,且烧得更厉害。几天里,弟弟的病情一直反复,后来浑身发烫、满脸通红,皮肤相继出现了血斑,医生说可能是毛细血管烧破了。母医院,可当时已腊月二十八,医院早已放假,去了也没医生。后来才知道,医院都有值班的医生。加之山路难行、路途遥远,全家人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村医身上,医生倒也尽心,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又从邻村刚死的一个孩子家里,拿来半瓶未输完的液体给弟弟输上,说这是从县里捎回来的好药,可输上液体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愈发加重,弟弟在急促喘气中,一声接一声地喊着爸妈,拳头紧攥、全身抽搐。最终,在大年三十来临的前夜,在父母撕心裂肺的呼唤中,弟弟永远闭上了他那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带走了全家人残存的一丝希望,留给全家撕心裂肺的痛。小小的他,静静地躺在床板上,像睡着了一样。母亲几乎发疯,父亲长哭不止,爷爷用一只大布鞋,在门槛上一遍遍拼命拍打,大声对天吆喝着弟弟的名字,希望把他未走远的魂儿再唤回来……母亲失眠的病根就是从这时得下来的!全家都很难接受弟弟离开的现实。弟弟小小年纪,就多灾多难,记得一个冬天,村里来了说书的瞎子,当时山村不通电,生活很枯燥,全年最盼望的娱乐,就是在农闲冬夜听瞎子说书,一个有趣的故事,往往一说就是十几天,每晚说到关键处就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清脆的快板和响亮的鼓点久久萦绕耳畔,精彩的故事情节让人身临其境、欲罢不能,白天忙碌的人们大都晚上早早地去学校听书,教室里的人挤得满满的。那晚我也随父母去听书,不到3岁的弟弟一个人睡在家里,半夜醒来后发现屋里没人,就一个人摸黑从床上爬下来想去开门,但因个子低够不上门栓,就爬上锅头,想再爬上旁边的水缸去开门,结果踩翻了盖水缸的箅子掉了进去,幸好缸里只剩半缸水了,但不知在这寒冬腊月天,他那嫩弱的小身躯在当时的冰碴水里受了多大的罪。直到半夜同院一个邻居大爷回家时,才发现了屋里传出孩子微弱的呻吟声,连忙叫回了父母。从缸里捞出弟弟时,他已冻僵休克,母亲把弟弟暖在怀里裹在被窝里,又熬了生姜红糖水,从孩子紧闭的牙缝里慢慢喂了进去,折腾了半夜才救回他的生命。当晚说书的瞎子听说后还随机应变,以“大人听书、孩子落缸”编了一段作为结尾。没想到,大难不死的弟弟这一次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亲戚和村里人的不断劝导下,悲痛欲绝的父母只能强忍悲伤,开始给弟弟料理后事。按当时山村里的风俗,山里几岁的小孩离世,一般都不埋,只是穿上衣服裹个席子,放到某条沟里或山坡上就行了。父母却舍不得弟弟,就找来村里最好的木匠,用最好的木料给他做了个小棺材,像安葬大人一样,把弟弟葬在了村西头一块朝阳的麦田里。人死难以复生,但葬完弟弟后,父亲又返回坟地久久徘徊,回来后给母亲说,真想把土扒开来,看看儿子能不能再活过来。那一个新年,全家人是在泪水和悲痛中度过的。干干净净的小箅子,还静静地晾在院里的窗台上,只是可怜的弟弟,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弟弟很小,但很听话懂事。刚上小学的他很爱学习,成绩很好,弥留之际还跟妈妈说,他的书本和作业本在哪里放着。记得那年9月9日毛主席去逝,弟弟在学校听老师说后,放了学就赶快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当时还叱责他说,谁说的?别胡说!当时的人们也难接受伟大领袖的去逝,追悼会时,天雾蒙蒙下着细雨,山村里的大人和学生全都带着黑袖章和小白花,在一个个花圈包围的大院,在黑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下隆重祭奠,不少人放声痛哭。在死亡面前,再伟大的人物都无能为力,更何况一个脆弱的小生命呢?第二年,父亲在弟弟坟头栽了两棵柏树,并经常去浇水看护,至今都已根壮杆粗叶茂。每年清明,我们都要去给二弟上坟,44年没有间断过。三弟、妹妹及我们的子女给他磕头烧纸上香,我久久地望着那个小坟堆,和郁郁葱葱的柏树,心想,如果弟弟还在,现在也已娶妻生子有一家子人了,我们兄弟姊妹在一起,该是怎样一幅美好的画面啊!可弟弟却早早地走了,留给我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童年黑白照片,后来我把照片翻印几张分别送给三弟和妹妹,留作永久的纪念。父亲走了后,我便将他和父亲的照片一起放在了家里祭祀的桌子上。那时的我只有9岁,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记忆中的母亲就是哭,不停地哭。不论过不过节日,她随时都会趴到弟弟的坟上哭。那几年,我最害怕找不到母亲,一不见她,我便第一反应去弟弟的坟上找。在空旷的田地里,瘦弱的母亲,伏在弟弟的坟堆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声哭,哽咽着哭,自言自语地哭,后悔不该让孩子去河里洗东西,后悔医院,后悔没有照顾好他……母亲在坟上常常要哭很久很久,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仿佛要哭尽她的生命才肯罢休。有时我一个人拉不回来,就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拉,往往是临近黄昏母亲还不起来,我们就连难受带惊吓地一起哭。后来得知弟弟得的病其实是出血热,该病大多是吃了被鼠类污染的食物后传染的,记得当时山村的老鼠很多,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有它们,人鼠争食,人们也是想了好多办法来治它,老鼠药、老鼠夹、老鼠网,但始终不能根治。在弟弟之后,姑姑家一个孩子也得了类似的病,母亲赶医院,医院后很快就治好了。那年山村流行出血热,没想到第一例就从弟弟开始了,后来的几例都接受了弟弟的教训,到医院后都治好了。可以说弟弟的早早离去,避免了后来更多生命的失去,他短暂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无论是被动还主动,只要你的人生为这个时代,哪怕是为某个地方的人发挥了一点积极的作用,那你生命的光芒就是美丽的。从此以后,母亲的精神就受到了严重打击,由过去的睡不醒到夜不能寐。失眠的痛苦如恶魔一般紧紧地笼罩着她。至今,虽已多次就医,但均无疗效,前几年还让她到外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后来母亲说,算啦,不治啦,熬一天算一天。现在每晚都靠高强度的安眠药,勉强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母亲生于年,幼年正是国家和家庭最困难的时期。母亲上完小学,就因家贫而辍学了。从此,十二三岁的母亲便随爷爷出圈担粪、采药拾柴,随奶奶挑水做饭、缝衣制布。一个寒冷的冬日,母亲又随爷爷去拾柴,爷爷挑大捆前边走,母亲挑小捆后边跟,母亲个子低,柴几乎挨着地面,过河时不慎被绊倒,人摔进了冰冷的河水里,一根柴尖刺中了母亲的额头,瞬间鲜血染红了河水,母亲挣扎着要爬起来,但却被柴捆压着,加之又冷又饿,浑身乏力,一直挣扎却难以摆脱险境。在前面行走的爷爷忽然回头不见了母亲,急忙返回寻找,突然见到河里流下的血水,爷爷吓得边跑边大声喊着母亲的小名,见到母亲时她已奄奄一息,伤口的裂缝如孩子张开的嘴,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头。爷爷迅速抱起母亲,从烟袋里倒出全部旱烟叶捂住伤口,又从衣服上撕下块布,简单按住伤口抱起母亲就往回跑。到家里奶奶把母亲抱在怀里大哭,爷爷叫来土中医,医生简单处理了伤口,又上了点麝香粉,用布裹住让慢慢愈合,至今母亲额头还留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疤痕。当时的土医生根本不懂消毒,也不会缝合伤口,村民再大的伤都靠自身造化和自然愈合,有的伤口常常感染化脓,热天里甚至长出蛆虫,有的得了破伤风病也不知道咋回事,因此而丧失性命的也不在少数。爷爷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姑娘,母亲最小。三个姐姐出嫁后,母亲便留在了家里照顾爷爷奶奶。后来,比母亲大十一岁的父亲来到家里,和母亲一起承担起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的义务。婚后几个月奶奶便去逝了。听母亲说,奶奶一生也多坎坷,从小因家里困难被送给了别人,在新家里不但没有温暖,而且受到虐待,常年睡在铺着麦草的窑洞潮地上,后来奶奶的父亲发现后才又心疼地把她领了回去,但从此却落下了咳嗽的毛病,最终在五十来岁时被肺气肿夺去了生命。奶奶长于困境但却生性善良,母亲说,教她小学的老师是个外地人,一次得了重病没人照护,奶奶便把老师接到自家,一边精心照护一边请中医调理,直到一个多月病轻后,老师的父亲才上山来用毛驴把他接走。奶奶和爷爷还先后帮几个侄子娶了媳妇成了家。奶奶的善行虽然没有延长她生命的长度,但却提升了她生命的质量,虽然我没见过奶奶,但却常听长辈们说起奶奶的好。我记忆中的奶奶永远是桌上的那张与爷爷合影的黑白照片,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奶奶比爷爷低多半个头、黑巾裹发、愁眉不展。据母亲说,当时爷爷和奶奶正在磨房里磨面,村里突然来了个照像的,母亲硬拽着爷爷奶奶出来留下了这张合影。山村很少来照像的,当时村里好多老年人的照片都是那次留下的。小时候,记得母亲经常给爷爷洗脚、剪手指甲和脚指甲,为爷爷剃头发、修胡子。在饥饿的年代里总给爷爷做好吃的,过年蒸的馒头,多是掺了大量白玉米面的白馒头,但最后母亲总要蒸一锅没有玉米面的纯小麦面馒头给爷爷吃。平时家里有点稀罕吃的也总是给了爷爷,爷爷又常常把好吃的给了我们。爷爷晚上睡觉前喜欢喝点小酒,家里再困难,母亲也没让爷爷断过酒。爷爷膝盖疼,母亲就托人从城里给爷爷买来护膝,晚上把白酒点燃给爷爷洗腿。爷爷一直活到88岁,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共和,在历经沧桑的淡然中,于年农历3月29日寿终正寝。我记忆中的爷爷很慈祥,永远是白胡须、黑衣服、深皱纹、高个子,裤脚系着白布带,腰里缠着黑腰带。爷爷去逝后,母亲哭着说她这下没有爸了。至今已30多年过去了,每年清明节,母亲在爷爷的坟前总要哭泣很久,而母亲的失眠也逐年加重。爷爷其实是我的姥爷,因姥爷没有儿子,我作为长子出生后,便随了姥爷的姓,由外孙变孙子,给姥爷叫爷爷。爷爷视我为掌上明珠,记得我从小就和爷爷一起睡,他晚上给我讲故事、猜迷语,临睡前喝一口小酒有时也让我抿一点,火辣辣地从嘴里下到肚子里,偶尔还让我尝一口他抽的旱烟,常常把我呛的双眼流泪。冬天他总是把被窝暖热了才让我睡,早上总是把我的衣服放在被窝暖热才让我穿,好吃的总是留给我。当时母亲奶水不足,爷爷便倾其所有到县城买来炼乳喂我长大。长大后,还见房子阁楼上放着两大筐我吃过的炼乳盒子和奶瓶子。后来弟弟妹妹出生后,家里就再没能力供炼乳了,只能用稀面汤、软面条喂他们长大。当时我全家7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大集体挣工分时,记得家里年年都是出钱户,日子过得很紧,全靠父亲的勤劳和母亲的计划勉强度日。后来包产到户,父母把田地当孩子一样精心看待,犁耙的很细致,田头地尾边角都种满了作物,绝不浪费一寸土地,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此全家才吃上了饱饭。母亲很要强,再难,过年总要让我们穿上新衣和新鞋,也很少让我们饿肚子,记得小时候好多家吃不上饱饭,而我上小学时却常常带着酸枣玉米面发糕,下课后和要好的同学分着吃。母亲在家里养猪养鸡做饭,忙完家务后就随父亲上地劳动或上山扛木头采药。很少见她有闲的时候,晚上我们睡觉时她总在灯下做针线活,早上起床时,也不知她和父亲什么时候就早早起来了。当时的母亲并不失眠,但却舍不得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现在才知道,早早叫醒他们的不是鸡鸣和狗叫,而是生活的窘迫和压力。家里再困难,父母都很重视我们的学习,我是我那一茬孩子中唯一走出深山到镇上读书的人,后来又考入师范。每次离开家,母亲总要给我包里塞满吃的,家里再没钱,父母就是借钱,也从未让我上学缺过钱,也从未短过学费,我的衣服和鞋子也是随季节及时换新。二弟不在后,母亲哭着把二弟用过的书包、课本、作业本和铅笔都放到二弟身边随他而去,希望吧他在天堂能继续完成他的学业,三弟学习不太好,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父母就把他送到刚成立的职业中学就读。妹妹初中毕业后,因犯头疼病在父母的遗憾中辍学,母亲后来常说,女儿若不是头疼,也能考个好学校。父亲个子不高,身单力薄,和母亲一起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很疼爱父亲,尽管偶尔也和父亲吵嘴,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力,母亲把父亲伺候的很好。每顿饭,母亲总让父亲吃最稠的,父亲和我们吃饱后,她才最后吃,剩多少吃多少,吃的往往是最稀的、最少的。父亲上山,给父亲备最好的干粮,父亲上地,就给父亲送饭。在我们眼里,他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忙碌,很少见有两个人同时闲下来的时候。晴天母亲多随父亲上地干农活,雨天父亲多在家帮母亲干家务,母亲做衣服,父亲就做饭,母亲纳鞋底,父亲就帮忙搓绳子。家里的一台老缝纫机和我的年龄一样大,那是母亲在怀上我的那一年,和父亲一起步行到县城买下的。据母亲说,那次和父亲一齐挑缝纫机差点饿死累死在山路上,第一天来到县城买下缝纫机后就住在一工作的亲戚家,当时城里的生活并不比农村好多少,粮食按人头定量供应,每顿饭都要精打细算,第二天清晨父母每人在亲戚家只喝了一小碗稀饭,吃了一小块发糕,便分开挑着上百斤重的担子踏上了百里山路,吃的那点食物很快便消化光了,肚子里空空的,走到半路一步也挪不动了,身出虚汗、心慌体软、眼冒金星,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看着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对母亲说,你去看看能不能讨碗热水喝,有气无力的母亲便艰难地走上前去讨水喝,好心的山里老婆婆给母亲端来半碗面汤,母亲和父亲喝了后,才觉得身上有了点点劲,硬是坚持着一步一步临天黑时才把缝纫机挑了回来,到家后父母都瘫软在了地上。可以说那次差点要了母亲的命,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半碗面汤父母一生未忘,后来路过此地总要看看老人,后来这家人不知去哪了,父母路过此地还要驻足观看,也常常向我们提起此事。在那饥饿的年代里,我们村还发生过一个放羊老汉用半个馒头救了城里一个干部的故事,这个干部后来当了某部门的领导,年年去看望老汉,直至老汉去逝。危难时刻,真情似金。从此家里一家老小的衣服,和村里不少家里的衣服都是靠这台缝纫机做的,它象父母一样永不停歇地辛苦操劳了几十年。忙碌平淡的日子在年被打破了。那年麦收前,父亲就吃饭少了,吃得也慢了。后来才知道,当时出现症状后,父亲曾给临村的一个朋友说过,说病在他身上,他知道可能得了不好的病。但父亲在家里却一直没有吭声,有时母亲问他,他也一直说没事,好着哩,硬坚持着和母亲一起把当年的小麦收完,晒干入仓。当时我已在县城工作,母亲见父亲吃饭经常打嗝,且越来越重,就捎信让我带父亲医院检查,我和父亲步行到了镇上,又乘公共汽车来到县城,到医院刚做完造影,医生就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爸的病不好,可能是食道癌,我如五雷轰顶、失声恸哭。第二天就和医院复诊,最终确诊,食道癌晚期,已扩散胃部,失去手术机会。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若不是收那茬小麦,若能早点发现做了手术,也许父亲至今健在。当时在父亲的心里,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可能比他的命还重要。母亲得知情况后,如山塌地陷、悲痛欲绝,一夜间白发骤增,不知她当时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泪,她既心疼父亲,又无可奈何,更熬煎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们商定不能在父亲面前表露痛苦和真相,只能在心里暗暗难受,从此,母亲就一人默默承担起了既伺候父亲又支撑全家人的重担。父亲平时也拄个棍子力所能及地做点家务,喂猪喂鸡喂牛,扫院子扫屋子,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又坚持和母亲一起艰难地收获了那一年的秋庄稼,播种了那一年的冬小麦。沉默的父亲始终也没问我们检查的结果,我们准备的"谎言"也始终未给父亲说,都在心照不暄地默默坚持着支撑着。除了我从外地捎点“对症”的药让父亲吃外,母亲只要听说有什么偏方就想方设法找来让父亲吃,一生没吃过药打过针的父亲,在那几个月里,不管多苦多难吃的药他都一声不吭地吃了下去,最后输液因血管细微难寻,多次扎不进去,父亲也一声不吭地忍受。我知道,尽管生活很艰难,但父亲也不愿早早离开,因为弟妹还小,他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后来,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吃下的东西很快就吐了出来,母亲就用一个罐头瓶子接着。给父亲捶背、推胸、揉腿、按摩,父亲整夜咳嗽不止,母亲就彻夜不眠地帮父亲翻身、喂水、接呕吐物,几乎夜夜如此。天亮后,一夜不眠的母亲还得操心一家子的事,给全家人做饭,地里的农活还不能耽搁,抽空她还要到附近山上给猪打草。父亲病的那段时间,母亲消瘦了很多,几乎失去了全部睡眠,我真不知道,那些天里她是如何熬过来的。世界上所有的坚强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困境中、在夹缝中硬生生地用生命挤压而成的,面对再大的困难甚至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坚持住了,你就成为了强者。在一个暖和的天气里,父亲带弟弟看了他栽下的一棵棵小树和大树,特别交待清了长在一块的树木,哪些是别人的,哪些是自家的。一天下午,他又把他仅有的元钱,默默地塞到了他最不放心的最小的妹妹手里。在冬末的一个残阳晒雪的日子里,他又艰难地带我看了他生前选好的坟地,那是他最终的归宿,从此父亲便再也没有走出我家的小院子。在第二年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日子里,耗尽全部气力的父亲,在母亲和亲人们的呼唤声中,听着窗外院子里匠人钉木做棺的响声,慢慢流下两行无奈的泪水,闭上了他那双深陷疲惫的慈眼,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操劳牵挂了一生的家。从此,平时很少叫爸的我便彻底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那几年,每当看到别人带着他的老父亲看病、洗澡、旅游时,我就多想再为父亲做一次。每当听到有关父亲的歌曲时,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夜里也常常梦到父亲而泪流满面。父亲生长在另一个小山沟里的美丽小山庄,从小失去母亲,长大后已到供销社上班的父亲为伺候患病的父亲,又辞职回家,作为长子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弟妹。因家境贫寒,三十岁时才经人说媒,来到母亲家做了上门女婿。父亲算盘打得很好,毛笔字也写得很好,一生爱干净,再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干干净净,地里干活再累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洗头,晚上洗脚、擦背,胡子稍露头就用剃头刀刮掉,脸上始终干干净净。他病重不能起床时也从不在床上大小便,总让母亲扶他到厕所,最后一次实在没力气了,才让我背着上厕所,背上的父亲轻飘飘的,让我心酸。此后十来天,父亲再未进食,也再未上厕所,他带着干干净净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记得小时候父亲曾背着我走亲戚,给我包书皮,给我辅导功课,上初中后为让我学习更好,给老师送山货,步行几十里山路,背着粮食送到学校食堂,担着柴禾送到我借宿的房东家,我考上师范后,天不亮就带着我走山路到县城赶最早的客车送我到远方去上学,用卖掉他亲手建的一座房子的钱供我上学,使我在三年师范期间衣食无忧……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生离死别的过程。父亲离开后,痛苦中的母亲更难以入眠了。她说最怕天黑,整宿整宿睡不着,就盼着天亮,天亮了又头昏脑胀、两眼发涩。她一边忍受失眠的折磨,一边又强忍悲痛,用病弱的躯体支撑着这个家。当时弟弟妹妹都还没有成家。在后来的几年里,母亲又先后给弟妹办理了婚事。弟弟妹妹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家庭成员在不断增多,但母亲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只有越来越严重的失眠伴随她漫漫长夜……我在县城工作,妹妹又嫁到了外地,后来因生活所迫,弟弟也出来谋生。老家只留下一个失眠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天独守着我们的老家。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独守空院,可能唯有忙碌,才能暂时驱赶她内心的凄凉和空虚。她一个人在家总不闲着,种菜、锄草、拾柴、养鸡、采药,家里院子堆满了柴禾,时不时地把一些土鸡蛋和萝卜白菜给我们捎到城里来。因交通不便,我很长时间才能回去看她一次,当时母亲的年纪并不算太大,但看着已经非常苍老了。一次村里人给我捎信,说你妈病了,我立刻找了车回去,见到母亲时,她两眼痴呆、表情僵硬、喃喃自语,神经接近错乱。我把母亲赶紧抱进车里,往医院赶去。她一路上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喊着弟弟、父亲和爷爷。这是母亲多年失眠加一些不顺心事造成的。医院后,医生给她注射了强力催眠针,才勉强睡了几个小时。从此,我下决心不让母亲一个人在老家住了,从那时起母亲才住到了县城。母亲的失眠最怕生气,她也最易生气,有时一句话不妥,她就生气。我们劝她,她也说实在不由人,一点不顺心,人不觉得病却觉着了。生气后失眠明显加重,晚上不但睡不着,还烦躁的厉害。回想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并没有让母亲少生气,特别是我,有时因一些事情和母亲看法不一致,在她不停歇的唠叨中,总忍不住大声说几句难听话,然后一走了之,也不管走了以后母亲如何难受。我成家后有了自己独立的小家庭,和妻子一齐养儿育女,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自己的小家上,往往忽略了母亲的感受,与母亲之间也经常产生一些缺少沟通的误会。其实我知道,不管平时母亲多爱唠叨,说话多不好听,她都是站在她的角度为了我们好。我也经常对她说,你好好照顾自己,别操我们心了好不好!可操了一辈子心的母亲却总放不下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圈子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母亲大部分的生活圈子都是这个家,最大也没出了那个小山村,家里的琐事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若没有这些琐事来“唠叨”,她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了,也正是这些琐事充实着支撑着她的生活和生命。其实家里的许多事本无对错,只是各自的角度不同罢了,只要能相互换位思考,就会减少好多误会和烦恼。有时我也想,母亲已这么大年纪,我们已无法改变她了,只能顺着她,忍着她了,有时实在忍不住,那是自己的修养和境界还不够。人常说,家有老是个宝,现在家里只剩下这一个老人了,她就是连接延续我们这个家族生生不息的根,根深才能叶茂,把根滋养好了,后辈才能兴旺。若一个家嫌老惯子,那是舍本求末,自伤其根,最终自酿苦酒,自吃苦果。我知道仍在失眠的痛苦中坚强地活着的母亲,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我们在顽强地坚持着支撑着她的生命。母亲搬到到县城后,却一直放心不下老家,只要有顺车,她总要跟回去看看,有时一个人还要在家住上几天。她一到家就不会闲着,不停地往家里捡柴,家里虽然没人,但整整齐齐的柴火却堆满了院子,仿佛随时准备着要回去长期住。最近村里依托景区优势,正在招商引资,发展乡村旅游,实行综合开发,老区人民纷纷将闲置的老院作价入股公司,进行老院改造,今天的善举将如种籽撒进土壤、绿满大地,破落的旧村将焕发生机,古老的家乡将重获新生,共同的家园将生生不息。我家的老院经母亲同意后也交了出来进行改造,母亲听说院子动工后,非要回去看着,总怕家里的东西丢,怕别人把活干不好,放不下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母亲在县城的家里常常坐着附近一些年龄相仿的老太太聊天,老家人下来,她只要看见就叫人家到家里吃饭。有时老家有人找我办事,找不到我,或者不好意思给我说,就找到母亲。母亲总是应承下来,吩咐我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容易,能帮的尽量帮。记得大集体时,家里也缺吃的,但省吃俭用的母亲总省下点粮食借济更困难的亲戚,村里来了讨饭的和流浪汉,母亲也常常拿出食物……母亲在县城住的小院里堆了不少杂物,废纸箱、塑料瓶、塑料袋,凡是能卖点钱的东西她都随手捡回,积攒多了就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现在生活好了,但她却从不倒剩菜剩饭,总是留到下顿热热再吃,她也见不得我们“浪费”,见了面总还是用她的观点来教育我们。被失眠折磨了几十年的母亲,常常心烦心燥、脾气不好、性格固执又不稳定,她和父亲相反,平时话很多,无论见到熟人或生人,她都有话可说,也不管别人愿听不愿听。大到社会大事、小到鸡毛蒜皮,她都有自己的“观点”,也不管别人的感受,心直口快、随性而说,无意中也会得罪人,好在了解她的人都不跟她见怪。母亲有时候也对我说:我话多,才活到了现在,难受的事说出来就好些,你爸不爱说,好多事憋在心里,结果憋了出毛病,早早就不在了。因失眠,导致她身体很虚弱,现在看着很胖,但那是多年吃药引起的虚胖。她一生动过三次手术,每次手术对她的身体都是一次摧残,同时也再次加重她的失眠。现在母亲的身体非常不好,免疫力很差,经常感冒咳嗽、腰酸腿疼,每年入冬都要感冒咳嗽很长时间,医院呆一个多月也效果不佳,医生说你妈用抗生素药太多了,现在输液效果都不好了,有些病她只能自己忍着扛着。而她的心却仍然很要强,看不惯的事还要说,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经多次“较量”,我是无法说服、也没法改变她了,只有尽量顺着她、忍着她、甚至哄着她了。药物是无法治疗母亲的失眠了,有时我想带她出去多转转散散心,看是否对她的睡眠有好处,于是在工作之余,和妻子、弟妹常常带她到周边邻县邻市的景点玩,还先后去了海南、河南、北京、西安等地,在景区母亲也曾露出灿烂的笑容,发出悦耳的笑声,但失眠却仍紧紧困绕着她,她常说我的头现在都成铁打的了,什么办法都不管用,你们也尽孝了,我火车也坐了、轮船也坐了、飞机也坐了,在咱村老婆婆中也算幸福的了,你们也不用再给我治了,熬了几十年了,熬一天算一天。最近几年,母亲的腰腿疼越来越重了,也出不了远门了,医生说这是年轻时出力太大落下的毛病。前几天,已步履蹒跚的母亲又随我们回去给爷爷上坟,没想到从坟前一个小坡坡下来时不慎闪了腿,虽然骨头未伤,但至今疼痛难行,走路都要扶着凳子一步步往前挪。世界上什么都可选择,唯有生出自己的母亲不能选择。现在,母亲的孙子一一我的儿子都当父亲了,母亲已是曾祖母了,刚刚一岁多的小重孙在母亲的怀抱里,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小太阳照得她红光满面,此时此刻的母亲犹如一棵苍老的大树,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颗珍贵的生命之果。母亲已经完成了她这一代人的使命,辛苦一生的母亲已没有多少事可做了,也做不了多少事了,她眼中的一切大事,其实都是与她往事相连的一些小事。人人都会变老,回忆往事,可能就是老年人日子里的主要内容。失眠犹如一个大铁筛子,筛掉了母亲的很多记忆,有时候近几天的事情她都记不起来了,明明说过多遍的话,却说从来没有说过。但筛不掉的东西她却记得很牢,爷爷奶奶父亲红彪的诞辰和祭日,她随口就可说出,令她高兴的伤心的甚至几十年前的一些琐事,她也记忆犹新。比如她小时候上学时的一些情节,说起来也丰富有趣:晚上老师告诉学生去开会了,其实并没有走,而是躲在窗外看学生自习,捣蛋的男孩把煤油灯挂在腰带上扭秧歌,被突然出现的老师吓懵了……最近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全国十几亿人被禁足出行、防止传染,这是年之后全国发生的又一件影响到每个人的大事,也是影响全世界的一件大事,母亲每天只能在小院子里活动,面对电视了解天下,每天又增加了多少感染人数,又死了多少人,她都很